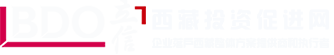現(xiàn)狀:
根據(jù)我區(qū)藏醫(yī)藥專家、植物學家、各企業(yè)等對我區(qū)瀕危藏藥材品種的選定進行收集和整理后,評選出西藏瀕危藏藥材有74個品種。
另外,他們將這些瀕危藏藥材品種劃分為三個保護等級,其中一級瀕危藏藥材有茅膏草、毛瓣綠絨蒿、白花龍膽、雞蛋參、冬蟲夏草、桃兒七、婆婆納、大花紅景天、喜馬拉雅紫茉莉等24種;二級瀕危藏藥材有藏紫草、雪蓮花、印度獐牙菜、忍冬果、土當歸、巖白菜等21種;三級瀕危藏藥材有柴胡、雪蓮花、綠絨蒿、亞大黃、螃蟹甲、亞麻、藏木香等29種。
同時,他們還根據(jù)我區(qū)藥廠需求量和區(qū)內(nèi)外市場需求,以及人工栽培研究的難易程度,對這74種瀕危品種進行了進一步分類。其中我區(qū)藥廠需求量大的有15個品種,分別為毛瓣綠絨蒿、傘梗虎耳草、唐古特烏頭等;市場需求量大的有8個品種,分別為高山大黃、冬蟲夏草、天門冬、鐵棒錘等;藥廠和市場需求量都比較大的有桃兒七、大花紅景天、波棱瓜、甘松、黃精等8個品種;人工種植研究難度較大的有茅膏草、毛瓣綠絨蒿、百花龍蛋、冬蟲夏草、金腰草、雪蓮花等12個品種。
保護:
“瀕危藏藥材保護方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快速開展人工馴化技術(shù)研究。”自治區(qū)藏醫(yī)院生物研究所所長扎西次仁說,接下來,自治區(qū)藏醫(yī)院將重點加強瀕危藏藥材的種子收集、種子質(zhì)量管理、種苗培育、品種選育等研究工作,同時結(jié)合部分已經(jīng)完成人工種植技術(shù)研究的品種,將嘗試推廣種植。
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所長蔣思萍表示,“可通過組培、調(diào)查來尋找新的藥材資源作為瀕危藏藥材的替代品,從而緩解瀕危藏藥材的采挖力度。”
記者了解到,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針對藏藥資源日益貧乏與藏藥材需求量不斷增加的矛盾,以西藏龍膽為例,他們完成了對高寒地區(qū)野生藏藥材——西藏龍膽人工種植技術(shù)的研究。
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組培研究室副主任尼珍介紹:“通過資源調(diào)查,初步摸清了西藏龍膽的分布情況,該成果首次在高寒地區(qū)對西藏龍膽的種子形態(tài)描述、種子分級、種子萌發(fā)技術(shù)、組織培養(yǎng)技術(shù)、田間栽培管理技術(shù)及生物學特性和萌發(fā)特性進行研究,篩選出種子分級指數(shù),確定了適合西藏龍膽種子的分級標準;通過種子處理,發(fā)芽率達到88%;平均生根率達60%,每株平均生根3到5條。移栽成活率達80%以上。而且首次對西藏龍膽野生種和栽培種的龍膽苦苷含量進行了對比,確定西藏龍膽栽培種中的龍膽苦苷含量整體上要高于野生種的含量。”同時起草了《西藏龍膽種植技術(shù)操作規(guī)程》,并在高寒地區(qū)建立了2000畝的西藏龍膽野生撫育基地。
建議:
記者從西藏奇正藏藥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為保護瀕危藏藥材資源,該公司建立了三類藏藥材基地,即保護基地、野生撫育基地、藏藥材種植研究基地。保護基地主要是重點保護具有青藏高原生物多樣性特征的藏藥材資源重要產(chǎn)區(qū),從而保證藏藥材種質(zhì)資源的可持續(xù)性奠定基礎(chǔ),如:米林南伊溝藥材保護基地;野生撫育基地主要是通過人工種植與野生撫育相結(jié)合來擴大和保證藏藥材資源供應(yīng)能力,從而在滿足市場需求量的同時,緩解對野生藏藥材的采挖影響,如藏木香、桃兒七、獨一味等等;種植研究基地主要是針對瀕危物種、需求大的品種、具有開發(fā)潛力的品種所采取的一種措施,如紅景天、矮紫堇、喜馬拉雅紫茉莉、藏丹參等。
據(jù)悉,西藏奇正藏藥目前在技術(shù)上有三大突破。一是產(chǎn)地適宜性種植技術(shù)方法成功應(yīng)用在野生撫育領(lǐng)域;二是對獨一味等80多種藏藥材資源率先進行了DNA特征圖譜檢測標準的研究和數(shù)據(jù)庫建立,這一科技成果獲得“國內(nèi)領(lǐng)先”的評定;三是將現(xiàn)代組培技術(shù)成功應(yīng)用在藏藥材可持續(xù)發(fā)展領(lǐng)域,大大提高了藏藥材資源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的效率。
西藏藏藥工程技術(shù)研究中心主任邊巴次仁說,隨著旅游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市場上出現(xiàn)了盲目推廣特色藏藥材的亂象,很多土特產(chǎn)店打著各種旗號出售紅景天、雪蓮、龍膽花等珍稀藏藥材,殊不知很多藥材只有經(jīng)過特殊加工后才能成為對人體有益的產(chǎn)品。這不僅對藏藥材資源是一種蠶食,還誤導了消費者,擾亂了市場秩序。“我們正在積極向有關(guān)部門呼吁,盡快出臺關(guān)于藏藥材保護與利用的三級目錄,即禁止開發(fā)利用的品種目錄、限制性開發(fā)利用的品種目錄、可開發(fā)利用的品種目錄。”邊巴次仁說。